“秋風葉兒黃,俺爹俺娘走在那山崗上、站在那河岸上,俺爹俺娘恩情一年比一年長……”11月4日,著名攝影家、紀錄片導演焦波做客敬敷大講堂,與現場師生暢談“從《俺爹俺娘》到《鄉村里的中國》,從紀實攝影到紀錄電影”,14萬余人次通過安慶師范大學團委抖音、安慶直播網網絡直播平臺聆聽了講座。

《俺爹俺娘》的攝影啟蒙
“1974年,我摸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臺相機,這對我有很大的觸動。”沿著時間的脈絡,焦波從“新”出發,跟隨時光的膠卷放映最初的少年模樣。焦波介紹,他用30年時間為父母拍攝了12000多張照片、600多個小時錄像,“我把俺爹俺娘從農村帶向世界,實現了‘用鏡頭留住俺爹俺娘’的初衷。”
焦波的母親晚年身高只有1.41米,體重71斤,是個裹著小腳的弱小女人;父親是村里的木匠,讀過4年私塾,《論語》倒背如流。在焦波眼中,爹娘是再普通不過的農民,面對拍照,他們鄭重、靦腆,甚至不理解。“平凡人為什么就不能做主角?我就要為農民寫‘史’,為農民立‘傳’!”1974年,焦波拿起相機,開始為父母拍照,他的紀實攝影生涯從此時啟程。

“爹說,當木匠要拉三年大鋸,鋸要一鋸一鋸地拉。娘說,推石磨就是抱著磨棍向前走,走一步就少一步。”作為焦波人生道路的啟蒙老師,父母在他心里是一本大書,一本永遠也讀不完的書。“爹娘用最樸實的話語啟示著我,做什么事情都要踏踏實實地向前走,走一步就離成功近一步。”
攝影要彰顯社會責任
反映時代變革的《爺倆》、見證改革開放的《老大返鄉》、昭示社會發展的《京城最后的掏糞工》……結合鏡頭定格的瞬間,焦波一一向大家講述照片背后的故事。無論是用虛化構圖帶來的動感,還是用對比的手法帶來的反差,在焦波的影像世界中,每張照片都是真實的時代印記。
上雀峪組圖是焦波拍攝的第一個圖片故事。在《淄博日報》當記者時,焦波發現了一個叫上雀峪的山村,那里嚴重缺水,多年來老百姓為了等水,每晚都抱著被子和水桶,睡在泉水邊。通過焦波的圖片報道,村里得到了多方幫助,打水井、建水廠,困擾數代村民的“用水難”得到了解決。
“村里打了水井后,我就去拍村民們咕咚咕咚喝水,圍著水井笑逐顏開的畫面。”最讓焦波記憶猶新的是,當時一位80多歲的老太太,顫巍巍走過來向他道謝,“老人握著我的手說:‘焦記者,等你退休了,俺們養活你。’當時她80多歲,我30多歲,誰養活誰啊?”可老太太話里的淳樸,讓焦波不禁感到身上沉甸甸的責任,也加深了對土地、對鄉村、對老百姓的深厚情感。
用紀錄片記錄鄉村這個更大的“爹娘”
通過鏡頭,焦波攬獲了國際國內多項大獎,但榮譽沒有影響他的進一步創作。他沉浸到貧困山村,選擇將鏡頭聚焦到最真實的生活中去,于是《鄉村里的中國》《出山記》《進城記》等一系列紀錄片在焦波手中誕生,記錄下一個個鮮活、樸素的中國人和中國故事。
拍攝《鄉村里的中國》時,焦波和他的攝影團隊走進鄉村、扎根鄉村,在373天的堅守中,與沂源縣杓峪村的村民們同吃同住,拍攝了數千個小時的中國鄉土畫面,“我們要記錄鄉村的改變,也要記錄來自土地和基層的真實。”
“老百姓在種地,我們在種植故事。”焦波生長于農村,對農村有著深厚的感情,他喜歡鄉土題材的作品,喜歡別人叫他“農夫導演”,“爹娘會拍完,但爹娘的‘爹娘’永遠拍不完,鄉村是我們每個人的爹娘,是中華民族的根。”
“老師,您怎樣看待農民這個階級呢?”“如果有時光穿梭機,您想對20歲的自己說些什么?”……講座結束后,圖書館東廳秒變“追星”現場,學生們紛紛提問。面對學生們提出的疑惑,焦波結合自身經歷深入淺出地為大家解答,并將簽名版《俺爹俺娘》送給了提問學生。
“焦老師給人感覺很樸素,他花了一輩子時間研究中國農村,這種工匠精神令人折服。”新聞學專業2020(1)班的張明星在講座結束后不禁感慨,每每提及中國農村,焦老師都會變得激動、振奮,那是對農民、農村最真誠的愛。(撰稿:王爽爽 楊帥 攝影:魏小婷 彭曉 審核:陳東 陳秀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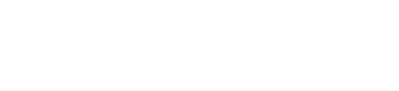
 安徽安慶菱湖南路128號
安徽安慶菱湖南路128號 郵編:246011
郵編:246011 安徽安慶集賢北路1318號
安徽安慶集賢北路1318號 郵編:246133
郵編:246133